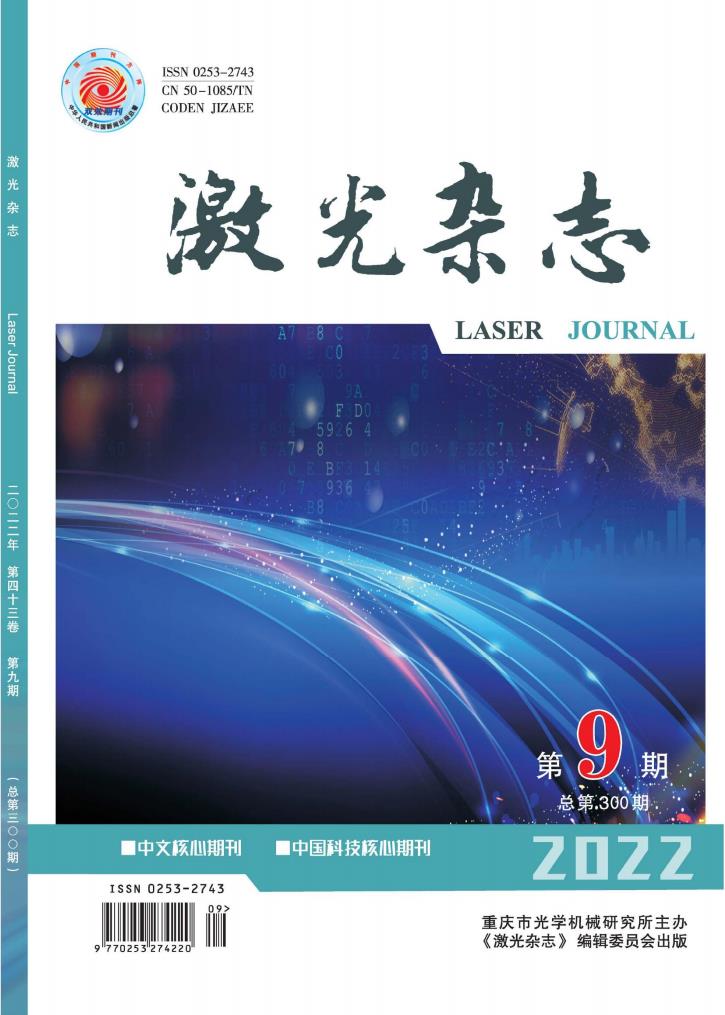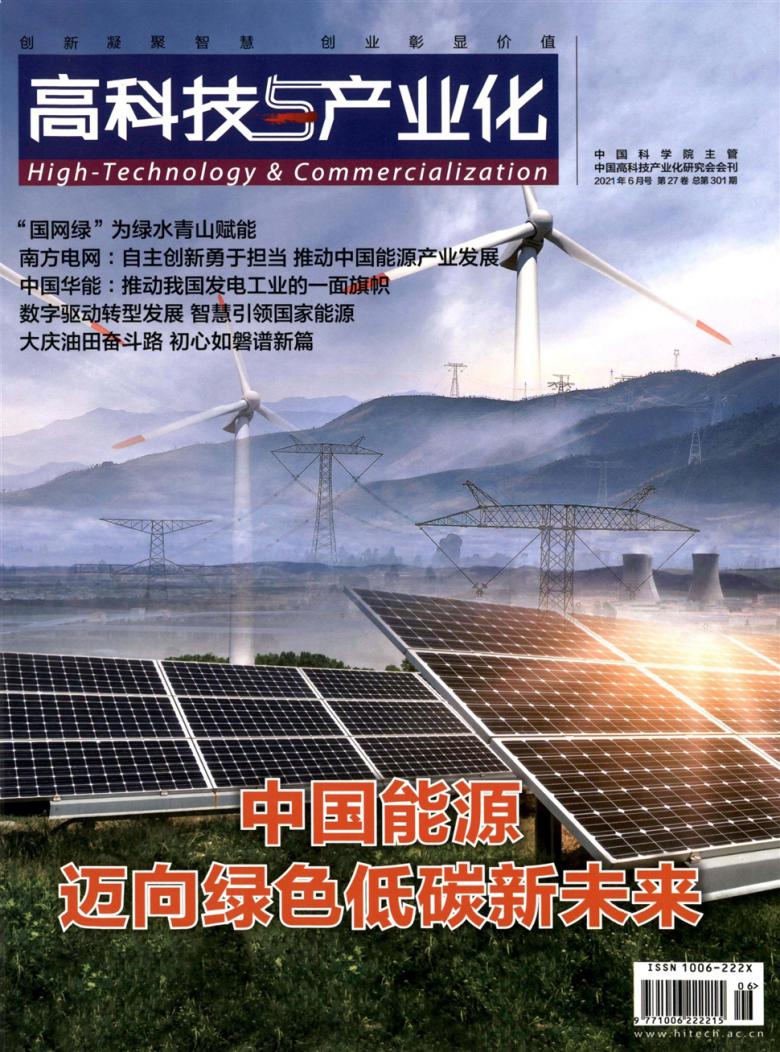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韩 昇 2006-04-05
【关键词】魏晋 隋唐 士族 统计 社会史
【内容提要】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魏晋隋唐社会的变迁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可以使该时代社会政治史更具有确定性,避免轻易的定性分析造成的以论代史,但也遇到史料不完整和不确定的障碍,对史料的选取判断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士族的特点是什么,与寒素、豪强、官僚有何区分,其向城市的迁徙具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研究中古社会史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基本问题。
一
毛汉光先生是台湾研究魏晋隋唐史学者,论著颇丰。2002年底,上海书店出版他的两本著作《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和《中国中古政治史论》。这两本书原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书中所论都是研究魏晋隋唐史的基本问题,我读后颇有印象。现在重读,又给了我仔细思考的机会。由于两书提出的问题,讨论起来颇费篇幅,故本文只介绍《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另外一本,另待机缘。
毛汉光先生出生于1936年,他们这辈人,在台湾学术界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在他们之前,是从大陆到台湾的成名学者;他们之后,是台湾培养的新一代,多为他们的学生。所以,他们的学术,从提出问题,观察角度,思辨模式,到论证方法,都可以看出中国学术传统的深刻影响。毛汉光先生本科就读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69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班,长年供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都与傅斯年先生密切联系在一起。傅斯年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与胡适之、蔡元培等先生提倡整理考订史料,揭橥“史料即史学”。此提法过于简单片面,引来许多批评。然而,考察史料学派所为,并不只是翻剪故纸,而是力图把中国朴学传统与西方的实证主义相衔接,探索新时代的史学规范,功不可没。公正评价史料学派,有助于我们今日重新确立人文学术规范,克服浮躁虚夸。
而且,毛汉光先生还曾经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员,接受不少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本书名为“社会史论”,就已经表明他试图用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古史,理论渊源,昭然若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不少中国史学家受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都曾经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史。由于这批学者国学功底好,又曾经留学,受过西学训练,所以,他们作出不少出色的研究,达到相当高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条研究之路中断了。几十年后,又有一批年轻学者重新踏上这条道路,人数增加,道路拓宽,水平也在提高。但是,也存在理论生硬套用,国学根基不够深厚等问题。因此,引进一些中西学术融合的好作品作为借鉴,无疑将促进学术的成长。毛汉光先生的这部著作,虽然不尽能满足上述要求,却也属于在此方面努力探索的著作,成败经验,给人启发,值得一读。
二
研究历史,首先必须牢牢把握对该时期社会生活给予重要影响的基本方面,也就是要把历史现象置于什么样的环境中去理解。正确把握这些基本点,历史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否则就沦为支离破碎、失去灵魂的断片。就中国中古时代而言,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造成的信仰崩溃和思想解放运动;随之而来的多次动乱,引起社会彻底瓦解而造成士族崛起,无疑是理解该时代的纲。这是一个人与社会互动的问题,更是人与文化合为一体的问题。或许读者看到这里不禁要哑然失笑,这岂不是常识吗?然而,我们却经常在常识上出问题,在历史学领域藐视对人的研究,甚至认为人物研究不属于学术范畴,因而抽掉人的经济、制度、法令条文的皮相描述,不是到处蓬生吗?在这一点上,毛汉光先生的把握是准确的,他在《序》中指出:“研究社会史最重要的是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经考虑,觉得欲研究官僚政治,先得明瞭社会背景以及社会中人物的特质,否则便仅能知官僚的空架而无法深究其内涵”。研究士族,分析士族社会的变迁,以此考察魏晋隋唐时代,可谓得其要。
本书共有十二篇,分为“总论”四篇,“分论”八篇。
“总论”四篇,分析中古统治阶层的社会基础,社会成分,中古家庭的变动和中古士族的演变。这四篇,作者对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政治进程作了一般性的概论,描述士族在此政治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并定义划分社会阶层的几个基本概念,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统治阶层的构成成分作了颇为细致的量化分析,用数据来说明该时期士族的产生及变迁,阐述士族社会与士族政治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作者的士族理论,统领全书。就作者的意图而言,“总论”应是全书的基础与灵魂。
“分论”八篇,是在“总论”理论框架内的展开和补强。
在中国中古史领域,陈寅恪先生是将西方政治学的党派政治与区域集团等理论用于具体研究,并通过一系列考证建立学说的先行者。除了众所周知的“关陇集团”说外,我们还可以从其弟子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中,窥见其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嬗替的精彩论述。受此影响,万绳楠先生也发表了论文《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1期),提出曹魏政权由汝颖和谯沛两大政治集团支撑,并分析其势力消长。较陈寅恪先生所谓曹魏为寒族、西晋为士族的区分法,要细致合理。毛汉光先生吸收他们的成果,在第五篇把研究扩大到魏、蜀、吴三国政权社会基础的分析,比较全面。当然,毛先生的着眼点,在于说明“单士”和地方豪族如何通过仕宦之途上升为士族,这个问题贯穿于全书,故后面几篇也围绕此主线展开。
第六篇,统计两晋南北朝主要文官中,士族、小姓和寒素所占的比例。第七篇则围绕唐高宗禁止陇西李、太原王、荥阳郑、范阳卢、清河崔、博陵崔、赵郡李等五姓四十四子相互通婚,亦即“禁婚家”展开,罗列这些家族成员的仕宦情况,分析唐朝修士族谱的目的。与此相关的是第十二篇关于敦煌文书中两件唐代士族谱残卷源流及修谱原则的论证。
第九篇统计唐朝十八个士族成员科举与仕进的情况,指出晚唐时期的政争,实际上是士族之间的争执,而不是武后以降新兴进士或中晚唐新进寒素进士与旧门第之间的互不相容,李德裕一党反对的不是进士第本身,而是进士的浮华风气。陈寅恪提出,牛李党争是寒素进士与旧士族之争,牛党拥护科举,李党反对。此说在唐史学界影响甚大,但实证薄弱。毛汉光先生的研究是有说服力的。关于此问题,傅璇琮等大陆学者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很值得参考借鉴。
第十和十一两篇,作了琅琊王氏和兰陵萧氏两个士族的个案研究,主要是统计这两个家族的仕宦情况,兼论其为人处事的风格。王氏的考察主要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代,萧氏则为隋唐时期,相互衔接,可以反映士族政治至唐不衰的一个侧面。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在中古社会史的把握上,毛汉光先生以士族为纲,以数理统计为基础,通过世家大姓在政治上的兴衰,揭示魏晋南北朝巨大的社会变迁。
关于士族的盛衰,士族门阀政治存续的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最主要的有两种观点,亦即认为士族门阀政治盛于两晋,而衰落于南北朝;另一类观点则认为隋唐仍属于士族政治时代,中晚唐以后才发生根本改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作了许多论证,反复辩难,推进了士族研究的深入。然而,辩论双方长期争论,却始终处于平行线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上颇有缺陷,亦即各自选取有利于己说的史料,拼辍整合,而没有对魏晋隋唐的士族进行总体的实证性评估;在具体考证上,又没有把史料作同时性和非同时性的区分,据以细分出若干时段;在空间上也没有区分不同区域,研究各自的特点。结果必然是以点代面,论证上脱离时空。在缺乏坚实的定量研究基础上做定性分析,必然随意性甚大,偏差甚远。毛汉光先生的研究,力图克服上述缺陷,把研究的出发点放在对士族的定量分析,整体统计从东汉末建安元年至唐末天佑三年(196~906)710年间,士族在官场的数量和比例。即使在能够运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的今日,要开展如此大规模的统计,也很不容易,迄今已发表的论著中,这是最完整的统计。而且,他还在时间上作更加细致的区分,共分为27期,从49年到20年不等,以25年居多,也就是基本上以一代人为一期,在中古史研究中,如果能真正达到此标准,那是非常精确的。
根据这份统计,可以清楚地看出,从东汉末年以来,士族在官场所占比例一直在上升,从建安年间的29%上升到东晋的80.8%,达到高峰。以后,南朝士族一直保持过半数的比例。我们知道,东晋后期,随着北府兵集团的兴起,出现了宋、齐、梁、陈的王朝更替,这四个王朝是由东晋时代不入流的军功家族建立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被称为“寒门”、“寒贱”、“庶族”取代了士族,实际上,国家政权仍由士族把持,只是不如东晋初期士族拥立东晋皇室那般“王与马共天下”的盛况,出身较低的皇族仍需要依靠盘根错节的士族来统治社会,时势使然。因此,政权更替的暴力革命,并不一定代表着社会革命。北朝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拓跋族起自塞外游牧民族,其酋豪阶层不同于汉族的士族,但进入中原以后,北魏政权中士族的比例在迅速提高,从31%猛升至79.7%,非但不亚于有士族门阀政治传统的南朝,甚至比同期的南方政权还要高。
为什么南北朝社会政治基础迥异,却发展出相似的士族政治社会呢?这是我们面对上述统计结果时首先想问的,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作者的关心似乎不在于此,颇可惋惜。我以为关键在于魏晋以来社会崩溃,基层组织全面瓦解,在国家体制外普遍形成自治团体,如战乱时期广泛存在的坞壁及其演变形成的自然村落,这些基层组织掌握在强宗大族手里,他们垄断乡村,左右地方政治,其强大者甚至影响中央,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都必须与他们合作、妥协,才能获得安定。 魏晋南北朝士族的强势,就在于其扎根乡村,拥有大量的人手,且由于魏晋以来的学术家族化,使得强宗大族获得文化的声望和影响力,地方势力、经济基础和文化权力结合而形成的士族,使得国家重新整合统一社会时,首先要把他们纳入国家体制之内,而后要将国家权力渗透入乡村组织之中,这必然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当然也是一个社会逐渐质变的进程。面对国家分裂造成的社会现状,新建立的国家政权都不能不重用士族豪强以获得统治基础,这就是南北朝都大量任用士族为官的基本原因。
由此看来,士族的存在是一种社会现象,同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国家政权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力、统治方式与技术能力、文化上的向心力、市场交换的频度与交通、传播事业的发达等方面相适应。尽管中国古代基本上是人治的政治,但是,人治不等于随心所欲的统治,也不能脱离社会存在的各种因素和条件。中国的统治形态,基本上与中国社会的发达成熟程度相适应。因此,士族把持的乡村社会不能在国家权力渗透下发生质变,则士族主导政治的局面仍将继续下去。这种社会内部的深刻变化,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是短期的、疾风骤雨式的暴力运动所能促成的。用“侯景之乱”或隋末民变之类孤立的暴力行动,举出若干家族衰败的事例,或者抽出几个单项指标就断言士族政治形态已经终结,那是轻率的。实际上,在社会动乱中,一些士族在动乱中衰落,另一批士族却在动乱中崛起,只要中古社会生产方式和基本形态没有重大转变,士族政治的格局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只关注动乱和个别人物的兴衰,是用人治的历史批判人治的政治。更何况摘取时论为依据的方法,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故反对者也容易摘取一堆描述士族政治兴盛的时论展开讨论,使得客观的史学研究陷入主观世界,价值判断横溢,以论代史。与此相比,毛汉光先生的统计,更有说服力。
社会的变迁,必须通过生产形态的转变、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变迁等诸多方面共同作用而实现,毛汉光先生的统计,证明了这个过程的长期性。整个隋唐时代,士族在统治阶层当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高,隋朝为67%,唐朝“安史之乱”前为65%左右,“安史之乱”后仍在56%到89%之间波动,越是唐朝后期,士族比例越高。然而,中晚唐士族比例异常之高,所反映的只是京畿地区的情况,因为藩镇割据以后,地方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地区的实际人事权力不在中央,所以,中央政界多士族是落日余辉的写照。除了这部分统计需另外探讨外,隋唐时代的统计说明,士族政治的局面依然维持。对于前述大陆史学界关于士族政治的争论,毛先生的研究做出了明确地回答,今后如果还想继续探讨这个问题,都不能回避毛先生构筑的平台。也就是说,必须有宏观统计的基础,哪怕是重新进行统计,也不能再用不完整的史料来立论。
三
数理统计有其优点,但是,要很好地运用于人文学科,并不容易,绝非加减乘除或者更加复杂的数理运算就能够进行。人的社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而且,表面看起来确定的东西,却必须进行定性的分类,才能够成为统计的材料。所以,定性和定量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可能简单地通过定量进行定性。这个过程,存在着许多歧义,需要历史的判断,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人文科学一旦运用数理方法,就不是简单容易的事。否则历史学界就没有历史学家立足之地,只要请来几位数学家就可以了。祛除数理术家对人学科的傲慢与偏见,才有社会文化的繁荣。
就本书而言,统计的基础是有疑问的。
首先,是数据选取的范围。毛先生以正史有传的人为基础,从中统计出士族所占的比例。这项工作虽然繁重,但也只能是典型分析,不能视为总体分析。因为史籍收载人物有其特定的标准和限制,收录的人物有限,因此不会是客观全面的。在此范围内,不管统计的人物有多少,都跳不出古代修史原则所规定的框框。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只有相对的准确性,可以作为理解一种趋势的参考数据。
正史收录的人物,以中央官员为主,难以反映出地方的情况。地方州郡一级官员,对于研究王朝人事极为重要。岑仲勉《隋书求是》大部分篇幅为隋代总管、刺史的考订,郁贤皓《唐刺史考》则是唐代刺史的专书,将来有志继续研究士族政治者,以这两部著作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必能推动研究进一步深入。
而且,随着考古事业的发达,碑铭墓志不断发现增多,提供了不少新鲜史料。毛先生在专题研究上,大量使用墓志材料,但在总体统计上,似乎未加统计。而且,书中对统计的原始数据未加说明,所以,我们对其统计的基础不清楚,也就难于放心利用统计成果。
其次,是对于数据的时间处理。本书大约以25年,亦即一代人为一个时段,将710年细分为27期,无疑是想让统计更加精确。对于为什么要区分为27个时段,书中有长达6面的介绍,然而,对于最为关键的史料数据如何准确判定时间,安插于这27个时段,却没有说明,故其统计结果,无从检验,我也只能根据这一时代史籍的基本情况来评论。
我们知道,正史处理传主的家世,一般在传记的开头作交待,述及其籍贯、数世先祖,文字极为简练,时间记载往往笼统含糊,有些人,我们可以参照别的传记、本纪等,对其活动的时间进行考证,但相当部分是无法确证的,即使有碑铭墓志可资利用,也难究其详。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对所有的数据作准确的时间处理,以适应作者25年一期的时段。而且,有不少官员的活跃年代,跨越几个毛先生划定的时段。因此,硬要区隔出这么短的时段,统计上应该会有不少重复统计和模糊统计。就中古时代而言,官宦士族在史籍中留存的人物多,时间长,而起自社会下层的政治人物收录少,骤兴骤衰。故本书对士族的社会统计,应该是高估的。所幸在总趋势上没有乖离。
在不完整和不确定的史料面前,相对的精确往往有较高的可靠性,绝对的精确则只有相对的可靠性。对于数理统计而言,实在是令人头疼的迷宫。作者如果不拘泥于自己设定的一代人时段,而取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做更大时段的划分,研究的结论也许会更可靠,更有意义。例如,西晋约50年,书中划分为两段,以“八王之乱”以后为一段。其实,从司马氏收罗世家望族立晋,其用人原则至惠帝相沿无改,“八王之乱”时,朝廷已失权威,宗王称兵,招降纳叛,任用附己,皆如流星,转眼即逝,这场贵胄大族的内讧,并没有树立新的用人原则,也没有社会阶层的兴替,看不出有划分为两期的必要。隋朝37年,书中合为一期,但隋文帝统治的24年,严厉镇压北周关陇集团权贵;炀帝则重用南方士族,用人路线颇有变化,倒是可以分为两期。在研究上,必须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研究的方法,而不能先决定研究方法,再拿研究对象试刀。
四
数据的处理,与对历史的理解颇有关系。对数据的正确分类,决定着统计的成败,而这项工作反映了学者对历史的基本认识和学养。正因为如此,所以带有相当程度的主观判断成分,也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容易引起争论。
毛先生对于社会阶层的划分,提出独特的标准。他把统治阶层的出身分为三类:1、士族:“采用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的标准以外,还添加凡史书皆称大族者”;2、小姓:“包括所谓县姓、地方酋豪、地方豪族等”,“是介于寒素与士族之间的阶层,依本文之定义,由寒素升为士族必需经过小姓这个阶段”;3、寒素:“指素士、农、工、商、兵、其他半自由民,及非自由民如奴婢、门客等”。 除了士族为学界通用的名词外,其他的小姓和寒素,都是毛先生的创新。
颇具社会影响的家族成为士族,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祖先世代官宦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文化要素也必不可少。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中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官宦加文化,是成为士族的必备条件。对此,毛汉光先生在理论上是赞同的(见第四篇第四节),但在具体运用上,却往往去掉文化的条件,在划分成分时,一再使用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为标准(第二篇第一节和第六篇第一节),以使得士族统计的面达到一定的数量级。这样做,在数据选取上标准明确,方便掌握,符合理科的要求。但是,“士族”却沦落为官僚“仕族”。“士族”和“仕族”大不相同,可资说明的事例俯首可拾。西晋宰辅贾充,先人做市魁,父亲贾逵为魏朝重臣,任豫州刺史,贾充助司马懿篡魏,女儿为晋惠帝皇后,岂止“三世中二世官居五品”,然而,当时人并不以其家族为贵,庾纯当面嘲笑贾充先人出自市井(见《晋书·庾纯传》)。研究者也未曾将贾氏列为士族。南朝权臣想当士族,求助于皇帝,皇帝说我可以升你的官,却无法让你当士族,除非你自个儿得到士族的认同,于是,这些权要屈尊拜访士族,骄狂点的想混个女婿当当,谦虚点的只想能捱着士族坐坐,却都受辱而归。至于已经获得公认的名门士族,数代无人当五品以上官,依然家门不坠,仰慕者众,这种事例更多,不暇例举。崔卢李郑王的社会声誉地位,堪称无冕之王,崔民干,唐初任黄门侍郎官,不过四品,唐太宗修《氏族志》,宰相们公推他为第一等,引来唐太宗愤愤不平,硬压低为三等,次于第一等皇族、第二等外戚,可依然高踞众氏之首。琅琊王氏,当然是名门,高官辈出,但王筠对于时人美誉崔氏和应氏颇为不满,致书诸儿论家世道:“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梁书·王筠传》)文化与官爵的关系及其社会评价,颇可玩味。中古时代,由于强大的士族豪强阶层存在,官本位未能完全确立。故依官品甄别士族,只能得其形骸。钱穆先生《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新亚学报》5卷2期)指出:“门第即来自士族,血缘本于儒家,苟儒家精神一旦消失,则门第亦将不复存在。”振聋发聩。
数理统计必然强调官位等外在形态,因此,就必须确立一些明确的、可以把握的标准。例如,本书第十篇就提出形成士族有三大主要途径:一是经过政治的主要途径,二是经过文化途径,三是经过经济途径,或由大地主、或由巨商大贾入仕。上面已经批评了将仕宦与文化分离的士族标准,至于第三条途径,则自惭孤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自汉初抑制商人以后,贱视商人的观念深入社会,并为后代沿袭。以商人富足、巨商大贾入仕来否定贱商观念,以为是一种悖论,其实是误解。除了汉武帝为解决军费而实行算缗告缗等特殊时期,抑商主要是政治、文化行为,防止商人挟富干政,凌驾贵族。因此,“抑商”并非“禁商”,在汉朝,早就是:“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汉书·食货志》),何况后代。商人可以富,甚至可以因为人治或腐败等原因绕过禁止商人当官的法规入仕,但不能获得国家统治意识形态或社会评价主体的尊崇,前述西晋贾充就是明显的例子。商人可以富,官人可以有权,但不能获得文化上的贵。所谓士族,是尊(财富、权势)贵(文化、精神)的结合体。就士族形成史而论,兹以贯穿中古时代的天下名门弘农杨氏为例,发迹于楚汉战争中将项羽分尸的杨喜,封侯高仕,然而要到东汉后期的杨震出现,以“关西孔子”的文化声誉蜚声海内,才真正被公认为士族名门。这中间经历了数百年的文化积淀,而人们评论杨氏,基本上是从杨震这时候开始,也就是从其确立为士族以后,而不再追溯到十几二十代远祖,因此,士族是历史形成的。尤其是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形成清浊的官人区别,官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清官,当有文化学识的忠臣,强大的激浊扬清舆论,促成知识阶层的自觉,形成尊重文化的士族标准。故士族一旦获得公认,就成为社会仰慕的对象,成为相对独立于统治意识形态的文化标准,不许清流所不容的寒人浊官商人巨贾所玷污,抵御政治入侵以至于唐朝,维系文化法脉,不绝如缕。在这期间,士族破落清贫者有之,数世未出高官者有之,却维持家门不坠,睥睨权势,怎一个量化标准把握得了?
小姓的定义,也令人困惑。在唐以前的史部著作里,只有两处出现“小姓”,说的是同一件事,一条是《唐会要》卷94记载圣历元年(698)八月,武则天想让武延秀纳突厥女,突厥可汗默啜拒绝道:“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小姓,罔冒为婚,我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另一条为《资治通鉴》卷206同一事件的记载,但默啜的文词略有不同:“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戸不敌,罔冒为昏。”显然,“小姓”是相对皇室而言,也是对武氏的蔑视。这同毛先生的“小姓”毫不沾边。毛先生创立的“小姓”,包含县姓、地方酋长、地方豪族等阶层,也就是史籍中“垄断乡曲”的豪强。然以“小”冠之,则似乎与士族有势力大小之分;若介于自由民、半自由民、非自由民的所谓“寒素”与士族之间,则又有高低之别。实际上,士族与豪强之别,在于文化立家,亦即士族本于儒家礼法形成门第,豪强则本于实力。豪强不一定小,士族不一定势力大,更不存在自由民、半自由民、非自由民先当小姓,小姓当官,然后“中央化”而成为士族的渐次攀登的唯一道路或模式。
至于“寒素”的名称,多见于该时期史籍文献之中。周一良先生早在1926年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4分册的长文《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中,已经指出:“凡非帝室而是清流者皆可曰素族,……南朝之称素族皆与宗室相对而言也。”并举出琅琊王氏等士族为例证。1983年,唐长孺先生在《读史释词》(《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又作了补充考证,指出素族实即士族的同义语,寒士为士人。显然,寒素指的并不是所谓自由民、半自由民、非自由民阶层。毛先生似乎也注意到此点,故于书中第二篇“分类”中说道:“在魏晋南北朝时,常有大士族称次级大士族为寒素、寒门。”但出注标明为其《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1968年)的发现。在社会阶层的具体区分上,依然坚持自己独创的“寒素”定义。
毛先生既然要把与“寒素”不相干的自由民、半自由民、非自由民合为一个阶层论述,就应该像“小姓”一样另外创立名称,不宜使用学界已有定义的名词,以免引起混淆。至于“半自由民,及非自由民如奴婢、门客”,到底有多少人跻身于统治阶层,完全应该统计出来,明示于书中。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对于社会阶层有严格的身份法律规定及限制,日本学者堀敏一先生专门出版了《中国古代的身份制——良与贱》(汲古书院1987)。奴婢成为统治者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正常情况下,法律上也不允许,因此,似乎应该作为一个特殊的现象,而不应同自由民混为一谈。
看来,数理统计的基础还在于对历史的把握。
五
士族是如何成为政治主角的呢?毛先生在第四篇作了回答,他认为在两汉社会,一端是代表政治力的皇帝,一端是代表社会势力的地方豪族,两者之间需要通过官僚与士大夫媒介沟通,这个中间人构成一个特殊的团体与社会阶层,地方豪族士大夫化,士大夫家族化,从而走向了中古士族之路。
那么,介于中央与地方豪族之间的士族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毛先生认为,汉代地方豪族占有土地而获得经济基础,但由于局限于一地而带有区域社会性,其宗族拥有一定的武装,构成武装团体。这种地方豪族必须有重大的质变,才能成为把持朝政的士族,最主要的变化在于要有学问,具备当官的资格,进而向中央迁徙,亦即要由社会性转变为政治性,由地方性转变为中央化,从而完成士族化的转变。因此,他归纳出其划分的士族、“小姓”、“寒素”三个层次之间的转化模式,也就是“寒素”经过“小姓”的阶段成为士族。
在此转化过程中,毛先生尤其重视“中央化”,把它作为地方豪族变成士族的必由之路。为此,他在第八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用100多页的篇幅,从两《唐书》和碑铭墓志中找出许多例证,罗列崔、卢、李、王、刘、高、裴、萧、薛、柳十姓十三家八十三房在有唐一代向两京迁徙的情况,又一次用统计数据来说明此进程。
所谓的“中央化”,书中第八篇“结论”定义为:“将具有地方性格的郡姓‘新贯’于中央地区并依附中央的现象”。亦即地方“郡姓”迁居并附贯于京城。在他看来,官僚化和中央化是地方姓族演变为士族的必由之路。
其实,官僚化和中央化是一回事,因为就官场而言,仕途都是以中央为指向的,官位晋升也就是向区域中心城市进而向京城的迈进,这种空间移动是以政治升迁为根据的,“中央化”是“官僚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所以,所谓的“中央化”,骨子里就是“官僚化”,这是以三代祖先的官阶决定士族与否的标准理所当然推衍出来的结果。看来,毛汉光先生太注重当官的经历了。
而且,其选取的十姓十三家都是士族,不能够说明“寒素”通过“中央化”上升为士族的过程。况且所统计的都是名牌士族,尚不足于说明士族整体的情况。就统计而言,取材是片面的。
从人员的流动,动态地把握社会的变迁,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值得充分肯定。如果从自己设定的框框中跳出来,将视野从官僚化这类政治史的问题拓展到社会史的层面上考察,倒是可以发现一个隐蔽却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随着国家统一的深层次发展,中央建立起文化主导权,并伴随经济发展和城市增多与繁荣,士族不由自主地从原来聚居的地方不断向城市迁徙,先是经由科举投身国家政治生活,而后更多人迁居城市,构成城市的文化阶层和生活消费群体,长年累月,与原籍地的宗族渐行渐远,完全城市化了,也就再也没有能力通过城乡呼应来影响政治,从而根本瓦解了中古时代士族的政治社会根基。城市化的士族依赖国家生存,构成国家官僚队伍;乡村士族因为上层精英分子不断被吸往城市而弱化,难以左右地方政治,成为乡绅。这是一个在不知不觉中展开的渐进过程,虽然缓慢,却造成质变,构成唐宋社会变革一个重要的方面。魏晋士族因扎根于乡村而强盛,至唐代因城市化而衰落,构成一部士族政治兴衰的历史。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另外撰文予以考察分析。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提出的问题是严肃的,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就触及到魏晋隋唐社会史的核心,值得我们再三深思,不断探讨。基于不同的理解,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毛汉光先生及诸位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