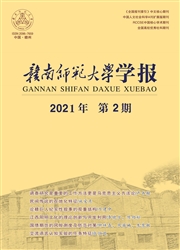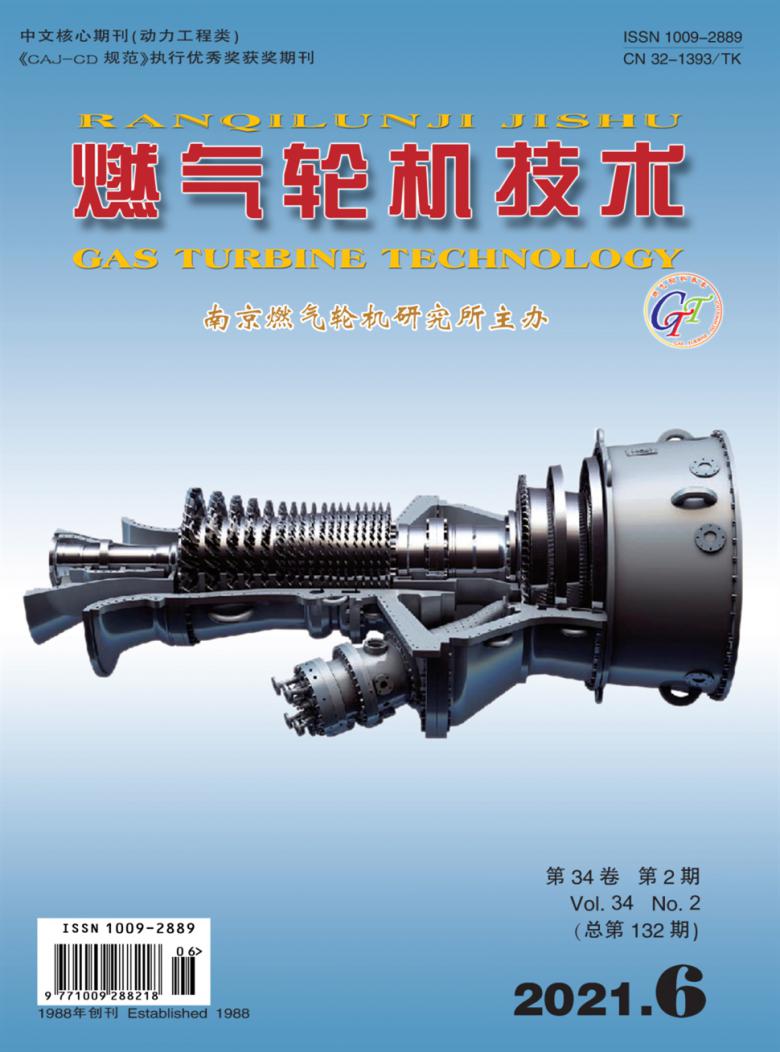从对寄生虫的认识看《内经》的人体观
潘大为 2009-09-08
【摘要】 从《灵枢·五味论》“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段的一个疑点入手,借助对《黄帝内经太素》杨上善注中“谷虫”“三虫”含义的探讨,证明《内经》对人体寄生虫的认识当中已经隐含了一个观点,即人体寄生虫的存在并不必然地导致疾病。这个观点较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若腑脏气实,则(九虫)不为害”之说的出现早得多,从而更全面地了反映《内经》对人体寄生虫的确切认识水平。杨上善注中“谷虫”“三虫”的含义也得到了阐明。
【关键词】 寄生虫;《内经》; 《黄帝内经太素》;杨上善
《内经》中“虫”的含义有二:一指自然界的“虫”,如毛介倮羽鳞五虫,主要见运气七篇;二指人体内的“虫”。有关人体内“虫”(以下简称“虫”)的记载涉及其致病的病因、病理、症状、诊疗,但对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虫”的存在是否必然致病,却并未交代,其中有隐含意义。
1 《内经》中的“虫”
《内经》明确提到的“虫”有两种,即《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的“长虫”和“短虫”,亦即《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脾脉)微滑为虫毒蛕蝎腹热”中的“蛕蝎”。史崧《释音》:“蛕蝎,上胡恢切,腹中长虫。下胡葛切,蠹虫也。”该句《黄帝内经太素》杨上善注(以下简称杨注) :“蛕,胡会反,腹中长虫也。蝎,胡竭反,谓腹中虫如桑蠹也。阳盛有热,腹内生此二虫,为病绞作腹中。”也就是说,常人腹内无“此二虫”。但杨上善这个平淡又正常的解释似与《灵枢·五味论》矛盾:“黄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气弱小,不能至于上焦,而与谷留于胃中,甘者令人柔润者也,胃柔则缓,缓则虫动,虫动则令人悗心。”“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是《内经》“五(味所)走”之一。“五走”是过食五味引起的症状。本段的“虫”如果也指“蛕蝎”,不免引起疑问:既然“虫”不是人人都有,用“虫”的活动解释饮食五味对正常人体的影响是否靠得住?要知道,《太素》和《灵枢经》对“五走”的记载基本相同,说明这些内容不但高度可信,而且古貌保存完好,这个疑点恐非文句错乱所致。更奇怪的是,《太素》杨注释该段的“虫”为“谷虫” :“甘味气弱,不能上于上焦,又令柔润,胃气缓而虫动。虫动者,谷虫动也。谷虫动以挠心,故令心悗。”
“谷虫”之说不见于《内经》。杨上善也没有解释“谷虫”与“蛕蝎”或长短虫是什么关系。看来,进一步探讨《内经》“虫”的意义是解释以上疑点的必由途径。从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以下简称巢《源》)提供的一条线索开始: “人有嗜甘味多,而动肠胃间诸虫,致令侵食腑脏……凡食五味之物,皆入于胃,其气随其腑脏之味而归之。脾与胃为表里,俱象土,其味甘,而甘味柔润于脾胃。脾胃润则气缓,气缓则虫动,虫动则侵食成疳匿也。但虫因甘而动,故名之为疳也……其上食五脏,则心内懊恼……” 该段像是《内经》“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的另一种版本。它描述了一种“虫动”所致的疾病,该病发病的诱因是“嗜甘味多”,故命名为“疳”。不过,与其说有意义的是该段与《内经》“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的相似之处,不如说是二者不相似之处—“虫”的含义。与《内经》相比,巢《源》对寄生虫的了解大为进步。但作为医书,巢《源》有一点不足:它受道教的明显影响。以“虫”为例,巢《源》的“虫”有时指“九虫”即九种寄生虫,有时指“三尸”,有时又是两者的总称。“三尸”作为生物与“九虫”的最大不同是,“九虫”是外源性的,“三尸”则与生俱来。两者常共同致病。该段描述的就是“三尸九虫,因虚动作”而致的匿病的一种。也就是说,该段的“肠胃间诸虫”有特定意思——既包括外来的“九虫”,也包括作为正常人体一部分的“三尸”。这使人联想,《内经》用“虫”的活动解释“多食甘”对人体的影响,是否暗示“虫”在人体内的存在是正常现象?杨注释“虫”为“谷虫”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2 “谷虫”与“三虫”
先看后一个问题。前面提到,杨注对“蛕蝎”的解释中规中矩;但在《内经》不指明“虫”的种类、概称为“虫”的地方,杨注就略微摆脱了“注不破经”之例的约束而有了发挥的空间。除上引“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段外,《太素·卷第二十七邪论·十二邪》(又见《灵枢·口问》)“问涎下”段杨注[1]也释“虫”为“谷虫”:“虫者,谷虫在于胃中也。……若因胃热虫动,故廉泉开,涎因出也。”
以及同样不见于《内经》的“三虫”。《太素·卷第二十气论·津液》(又见《灵枢·五癃津液别》)“中热胃缓则唾出”段杨注 :“虫者,三虫也。……谷消之时,则虫动上下,肠胃宽,充郭中,故肠胃缓而气上,所以唾也。” 为什么杨注释“虫”为“谷虫”“三虫”?“谷虫”“三虫”与《内经》的“蛕蝎”或长短虫是什么关系?回答这些问题要首先澄清“谷虫”和“三虫”的关系。同一个症状(“唾出”/“涎下”),为什么“中热胃缓则为唾”段杨注释以“三虫”,“问涎下”段杨注又释以“谷虫”?从两处杨注所依的《内经》原文判断,“三虫”即“谷虫”,两者是一“虫”二名。两段描述的是同一个病理过程:
中热(胃中有热)-虫动(虫上下作)-胃缓-气逆(廉泉开)-唾出(涎下)“唾出”或“涎下”都是这个病理过程的结果,差别只在于文字表述。这不但反映出《内经》不同篇目之间的契合呼应,也证明了两处杨注分别提到的“三虫”和“谷虫”所指相同。再来探讨“谷虫”和“三虫”的具体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巢《源》把“九虫”中的三种也称为“三虫”[2] : “三虫者,长虫、赤虫、蛲虫也……此既是九虫内之三者,而今别立名,当以其三种偏发动成病,故谓之三虫也。”
根据《太素》杨注与巢《源》著作时代的接近、以及《内经》“唾出”与巢《源》“九虫病”症状“多唾”、“流涎”的类似,可以确定,杨注的“三虫”与巢《源》“三虫”有类似的含义。
那么,为什么杨注又把“虫”释为“谷虫”呢?答案来自日本江户时代医家森立之的启发。森立之《素问考注·咳论篇第三十八》 [3]:
“东方朔《神异经》云:‘人腹中蚘(按:即蛔)虫,其状如蚓,此消谷虫也。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知蚘虫常居肠胃中也。案:《神异经》似可从。余曩在相州日,亲见鸬匠,以鸬取年鱼者,鸬之喉后以铁环锁之,令鱼不入胃中。若是铁环少缓,则顷刻间鱼头入胃之处,纵横蚀缺。云:‘鸬鹚腹中有千万蚘虫蚀之之所为也。’乃与《神异经》所说相符,盖人物一理,或是然矣。” 《神异经》 清代学者认为系魏晋人托名东方朔所作,现在一般认为系汉人作品,也就是说,其成书与《内经》形成同时或稍后、又在杨上善撰注《太素》之前。其内容虽属“小说家言”,但宏诞迂夸之说也要以某些事实为基础(如“鸬鹚腹中有千万蚘虫蚀之”是对胃酸作用原理的想象),从而曲折地反映其时通行的某些观念。森立之提出了猜想却没有深究,恰好使我们将杨注“谷虫”问题与他遗留的问题一并解决。《神异经》称“蚘虫”为“消谷虫”,杨注释《内经》的“虫”为“谷虫”,二者字面的相似出自一种共识:“虫”能“消谷”。实际上,这种认识在《内经》中就隐含了。《灵枢·上膈》:
“(寒汁)流于肠中则虫寒,虫寒则积聚,守于下管……人食则虫上食,虫上食则下管虚。”
“人食则虫上食”说明“虫”以人所食——即水谷——为食。在这个意义上,称“虫”为“谷虫”或“消谷虫”不无道理。“虫”(“谷虫”)在人肠胃之间的不同活动,如上下、聚散,反映为寄生虫病的多种症状。《太素·卷第二十六寒热·厥心痛》(又见《灵枢·厥病》)“心腹痛,憹作痛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善渴涎出”杨注:“虫食而聚,犹若肿聚也。食已而散,故休止也。又聚扰于胃,故热渴涎出也。”
可见“问涎下”段杨注“谷虫在于胃中”,是指寄生虫“聚扰于胃”使人流涎,并不是说在《内经》所说的“蛕蝎”(或长短虫)之外人胃中另有一种“谷虫”。“谷虫”即“蛕蝎”(或长短虫)。 所谓“虫”能“消谷”,实质是“虫”与人争夺营养,并非“虫”替人消化水谷。但“谷虫”或“消谷虫”的称呼,很容易使人误会“消谷”是“虫”对人的正面作用。《神异经》说蚘虫“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后半句犯的就是这个错误。森立之对这个错误也没有察觉,反而由此得出“蚘虫常居肠胃中”的结论,则是错上加错。后世与森立之结论类似的说法,如《医方集解》“蛲蛔为人身所当有之虫”,可能也是从这个误会来的。
3 寄生虫病
尽管结论错误,森立之却已经触到了《内经》中的一个灰色问题:“虫”在人体中的存在是否一定导致疾病?
《内经》在这个问题上颇不坦率。在《内经》有关“虫”的九处记载当中,对“虫”的称谓却有3种:单名〔“蛕(蛂)”“蝎”〕;双名(“长虫”“短虫”);不涉及种类的概称(“虫”)。使用单名“蛕”“蝎”的地方专注于“虫”的致病作用,如上引“(脾脉)微滑为虫毒蛕蝎腹热”。相反,使用双名“长虫”“短虫”的地方似乎倾向于将“虫”视为一种无害的存在,只是在某些情况下致病,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篇》:
“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 该二句又见《太素·卷第十四诊候之一·四时脉诊》,可见其说甚古。最蹊跷的,是不以“长虫”和“短虫”之有无、而以其多少论病。看起来似乎可以这样理解:“长虫”“短虫”只在数量多的时候致病并在梦中有所反映;人体内存在少量“长虫”“短虫”则完全正常。这与巢《源》的著名论断有点相似 [2]:
“九虫……人亦不必尽有,有亦不必尽多,或偏有,或偏无者。诸虫依肠胃之间,若腑脏气实,则不为害,若虚则能侵蚀,随其虫之动而能变成诸患也。” 即使退一步,按《新校正》的意见,这两句不属《内经》而系“他经脱简”,也足以证明,与《内经》并行传世的有这样的观点:“虫”在人体中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疾病——可见,巢《源》对人体寄生虫的中庸看法,早在《内经》形成时期就初见端倪了。
既然认为“虫”在人体内的少量存在是正常现象,为什么《内经》中并不予以说明?原因可能是《内经》流传过程中的文字亡佚,也有可能是象巢《源》所说“脏腑气实”则肠胃间的“虫”不能为害致病,其存在也就不被注意。很可能,“虫”在人体内的存在还是在“虫”病的症状十分明显之后才被察觉的。所以,对“虫”病的讨论占了《内经》有关“虫”的记载的几乎全部篇幅,并不奇怪。相形之下,令人称奇的倒是存在于人体但不为患的“虫”在《内经》中仍有蛛丝马迹了。
4 “虫”的普遍存在
分别使用单名(“蛕”“蝎”)和双名(“长虫”“短虫”)的,是对“虫”在人体中的角色的两种不同意见。两种意见俱载于内经,是上古时期不同医学流派共存、争鸣的反映,也是《内经》成书过程的缩影。那么,不问种类而概称为“虫”的地方又如何呢?仍以“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为分析对象。该段描述的病理过程如下:
多食甘-胃缓-虫动-悗心
如果认定“虫”在人体之中的存在必然导致疾病,那么鉴于《内经》对“五走”中另外四个的解释都以生理机制为依据,用一种致病原的活动解释饮食滋味对人体的影响的确格外可疑,但毕竟只是可疑而已,不能由此排除该段视“虫”为致病原的可能性。
然而,将该段与《灵枢·五癃津液别》“中热胃缓则唾出”《灵枢·口问》“问涎下”对照,就不难看出,尽管“悗心”和“涎下”“唾出”一样,是“虫动”的直接结果,但“悗心”并没有象后两者一样被说成是“虫”的活动引起的症状—即寄生虫病的症状。相反,该段把“悗心”归因于“多食甘”。但既然“悗心”与“多食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多食之(甘)令人悗心”之说的普遍成立就必定以一种观点为前提:“虫”在人体内普遍存在。
这种普遍存在并不指人人都患有寄生虫病,但它意味着,在某种能使“虫”由蛰伏变为活跃的诱因之下,虫的活动引起的某些症状——如“悗心”——就有可能在人身上普遍出现。“多食甘”就是这样的一个诱因。而把这种症状归因于“多食甘”而不是“虫”,只是为了强调“多食甘”有诱发这个症状的作用,并不是对“虫动”与“悗心”的因果关系的否定——上引巢《源》对“疳”病之名的解释可作这个解释的佐证。也就是说,“虫”在人体内虽然普遍存在,但除了少数情况,“虫”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疾病。
显然《内经》该段隐含的这种观点与使用“长虫”“短虫”之称的《内经》篇目的观点一致。而这个观点并未反映于该段或其它地方的杨注。杨注“谷虫”之说与《内经》这个观点貌似有关,却没有实质联系。
以人体寄生虫学观点看,这种看法实属对寄生虫的危害认识不清,但与专注于“蛕蝎”致病的观点相比,《内经》部分篇目中隐含的这种看法,或许更全面、也更充分地反映了上古中国医学对人体的实际考察和思考方式。